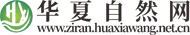【世界新视野】5.8、曹雪芹为何要翻案好色不淫并说古今之情大都是淫
 (资料图)
(资料图)
点击蓝字关注“幽之鸣”
梦游太虚幻境的贾宝玉听完红楼十二曲之后,警幻仙子给他讲了一段情淫训解之辞。忽警幻道:“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红楼梦第五回》)这一段是曹雪芹通过警幻仙子表达他对世人之情的看法。警幻仙子先是对尘世富贵之家的淫污纨绔与流荡女子进行了批判,她认为这些人淫滥放荡,行风月事于绿纱窗下,只顾在女儿绣阁中行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绿窗风月,绣阁烟霞早已不是清白女子之雅居,成了风流浪子寻花问柳之淫场。警幻仙子此段话其实是对历来野史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批判。因为历来野史与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风流轶事大都发生在女儿的闺阁内外,绣阁成了吃瓜群众街谈巷议的招牌。自古以来,这些轻薄浪子都自称“好色不淫”。他们为了将自己“好色不淫”的观点合理化,于是将自己的行为美化成是因情之所至而彼此投契,以情而不淫作案。但是在曹雪芹看来,好色不淫与情而不淫都是掩丑饰非之语,他认为好色即淫,知情更淫。为何这么说呢?曹雪芹给出的答案是:“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说好色不淫,情而不淫者都只是为了让世人觉得自己不淫,但最终又难免不会有“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的作为。“好色”指的是喜好对方花容月貌的美色,如果说好色不淫、情而不淫者最后没有“巫山之会,云雨之欢”,其与异性相交不过是平常之交,也就不存在好色一说,更不会涉及淫。但是好色者最终都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作结,好色的最终目的不过是娱自己肉体皮肤之欢畅。这不是淫,又是啥呢?所以说好色即淫。我们论证此结论的前提是在一个人与不认识的异性初见时,对其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只喜好其美色,然后将喜好对方的美色当成是情。情不过是喜怒哀乐已发的产物,情之已发本就不是真情,发而不中节,只以色为导,不过是因为感官受到外界的刺激而产生的一种假情罢了。故意将这种假情当成真从而欺骗世人,以达到自己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的目的,这岂不是更淫。所以说知情更淫。这正如鸳鸯死时,秦可卿之魂对鸳鸯所说的话:“你还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欲之事当作‘情’字,所以作出伤风败化的事来,还自谓风月多情,无关紧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便是个性,喜怒哀乐已发便是情了。至于你我这个情,正是未发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样,欲待发泄出来,这情就不为真情了。”(《红楼梦第一一一回》)这些轻薄浪子将淫欲之事当成情来看待,最后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来。轻薄浪子还自称风月也是多情之物,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营造出天底下全是多情种的氛围,从而使自己的多情合理化,让世人觉得他们的多情行为无关紧要,因为全天下都是多情种,所以自己多情也合理合规。这些轻薄浪子不过是用情来掩丑饰非,为自己行风月之事图一时舒爽找借口,从而合理化自己的淫欲。情之已发全是假,知情岂不是更淫。甲戌本侧批对警幻仙子说“好色即淫”批道:“好色而不淫”,今翻案,奇甚!“翻案”指推翻前人的定论,批书人提示我们,曹雪芹的立意就是要推翻前人“好色不淫”的观点。曹雪芹要推翻哪些人“好色不淫”的观点呢?在第一回顽石向空空道人解说其书的好处时,给了我们答案:“……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红楼梦第一回》)作者利用顽石先是批判了历来野史与风月笔墨,历来野史全是些淫滥之词,这些文字写的全是讪谤君相,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之事。风月笔墨又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将子弟都教坏了。作者接下来重点批判了才子佳人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虽多,但都采用同一个套路,且最终都不能不涉入淫滥。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主角全是如潘安、子建一样的人物;女主角全是如西子、文君一样的人物。潘安即潘岳,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俊美男子。子建即曹子建,子建之才,《南史谢灵运传》有载:“灵运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子建才高八斗由此得来,后世用曹子建代指极具才学的人。西子即西施,她被誉为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貌若天仙。文君即卓文君,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才女,才华横溢。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女主角个个才貌双全。既有绝世外表,又有绝世才华。因为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主貌比西子,所以男主一见便神魂颠倒。又因为男主英俊潇洒,所以女主一见就心醉神迷。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当属《西厢记》,其中的男主张君瑞见了崔莺莺后,写的是:“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宠儿罕曾见。则著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见了万千女子的张生从未见过像崔莺莺这样美貌的人,这不就是警幻仙子说的既悦其色,复恋其情吗?这不是淫是什么呢?如果不是淫,那么张生在见了万千别的女子时何以没有这样的行为?何以没有与其他万千女子中的一个共赴一生的想法?张生对崔莺莺的最后做法是:“我将这纽扣儿松,把搂带儿解。”“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但蘸着些儿麻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揾香腮”“谢小姐不弃,张珙今夕得就枕席,异日犬马之报。”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张生对崔莺莺的情最终还是以淫滥收场。这好色不是淫,就问是什么?如果我们对历来野史、风月笔墨以及才子佳人小说进行深究细查,就会发现大都自相矛盾,都是大不近情理之文。这些文章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不过是为其淫而饰非掩丑。世上的野史、风月笔墨以及才子佳人小说如此涂毒笔墨,将我们中华民族真正优秀的诗礼文化糟蹋,使很多不明所以的人认为诗礼簪缨之族的文化全如才子佳人小说所写的那样,觉得世家大族的家长与儿女都是些不近情理之人。所以曹雪芹要拨乱反正,翻案好色不淫之语。要让世人认清什么是诗礼簪缨之族真正的文化。让世人不要被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故事带偏,让世人认识到真正的世家大族并不像才子佳人小说里所写的那样。作者通过贾母写出了这一点:贾母笑道:“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人满腹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法就说他是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不成?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再者,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便是告老还家,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鬟?你们白想想,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众人听了,都笑说:“老太太这一说,是谎都批出来了。”贾母笑道:“这有个原故:编这样书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编了出来取乐。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别说他那书上那些世宦书礼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也没有这样的事,别说是那些大家子。可知是诌掉了下巴的话。所以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这几年我老了,他们姊妹们住的远,我偶然闷了,说几句听听,他们一来,就忙歇了。”(《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贾母一段话将才子佳人小说中不近情理之处分析得极其透彻,此回回目叫“史太君破陈腐旧套”,曹雪芹所要破的就是历来野史、风月笔墨以及才子佳人小说所写的那些不近情理的陈腐旧套之文,从而还真正诗礼簪缨之族的本貌。贾母的解释让我们明白了真正世家大族培养出来的家长与女儿,并不像才子佳人小说里的人物。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出生必是书香门第,她们的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既然是世家大族的女儿,必教其知书识礼。这些女儿无所不晓,个个才比文君,貌比西子,是世上的绝代佳人。但就是这么个知书识礼的人,一见到清俊的男儿,不知其底细来历,话都还没有说上一句,便对其一往情深,一见钟情,一心只想着自己的终身大事,想邀约着与这个男子私奔。父母不要了,书礼也没了,将自己变成鬼不成鬼,贼不像贼,这样的女儿在贾母看来并不是真正的佳人。虽然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子个个才比子建,但是对于初见这个才子的佳人来说,她与这个男子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对对方的底细都没有弄清楚,便对其一见钟情。只凭一两首情诗艳赋便断定对方有才学,真是可笑至极。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情节显然不合情理。贾母当着这么多姑娘小姐们的面说得相当委婉。用警幻仙子的话说,像崔莺莺一样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主其本质就是淫。为什么说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这些女子的行为是淫呢?因为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子个个貌比潘安,这些女儿只初见了清俊小伙一面,就被其美貌所迷,连对方的底细都没有弄清楚,不管是亲是友,就什么也不管不顾起来,只想着自己的终身大事。这不就是只悦其容貌吗?悦其容貌不就是好色吗?按警幻仙子“好色即淫”的说法,这不就是淫吗?陈寅恪先生在《读莺莺传》中通过一系列论证得出了以下结论:“然则莺莺所出必非高门,实无可疑也。”在论证崔莺莺并非真正的高门时,陈寅恪先生用了假设法。而曹雪芹却用他真实诗礼簪缨之族的经历,同样得出了崔莺莺是假托高门的结论,真正的高门闺秀绝对知书识礼,绝不会做出崔莺莺所行之事。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又满腹经纶,他们的才可比子建。有大才者必有大德,有大德者必不会乘人之危。张君瑞遇崔家有难,作为读书人如果有能力帮其解除危难,理当义不容辞,绝不会因对方拿女儿作为酬谢才去救。在解救之后也应有一份洒脱与豪放,而不是将这次解救作为一桩交易,将崔家之女嫁给他作为条件,这样的救与那个叛将孙飞虎想娶崔莺莺做压寨夫人有什么区别,都不过是乘人之危。如果因为对崔家有恩,把崔莺莺当成报恩的工具。这样的人算得上有大德的人吗?不过是为了一己私欲。既然没有大德,又何来大才之说。如果张君瑞果真不是贪念崔莺莺美色,他何以在不了解崔莺莺的为人品行时,就一心认定崔莺莺是自己的未来呢?还不是被崔莺莺的绝代仙姿所吸引,他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好色。张君瑞如贼一样与崔莺莺偷情,这哪里是知书识礼的人所能干出来的事。所以贾母说满腹文章去做贼,这些所谓的才子实是入了贼情一案。这哪里算是才子,人家女儿一直在深闺之中,从来没有见过世面,这样勾引着别人女儿行苟且之事,张生的行为放在现在是妥妥地拐骗良家少女。如果张生是真正知书识礼的才子,绝做不出没有给女儿名分便与其偷情的事来。可见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主角也有诸多矛盾处。世宦之家不只是小姐知书识礼,就连夫人也是知书识礼的。这样的大族人家就算是告老还乡,也还会用许多的奶母丫鬟来服侍小姐,绝不会出现只有一个丫鬟服侍小姐的情况。《西厢记》中只有一个红娘服侍小姐的情况在世家大族中绝不可能出现。服侍小姐的丫鬟也会经过精挑细选,但是这个丫鬟也绝不可能像《西厢记》中的丫鬟红娘那样,开口便是者也之乎,非文即理。能说出者也之乎的人,一看就有学究气,其一定受过老学究的教导,既然有老学究教其读书,其家境也不会太差,这样家境的人又如何会让自己的女儿去做丫鬟。做丫鬟的大都是穷苦人家的女儿。非文即理的意思是:不是说着极有文采的话,就是说着极深奥的道理。就算这个丫鬟真的知书识礼,怎么会引得自己的小姐与不熟悉的男儿偷情。更何况世家大族中的丫鬟压根就没有读过什么书,这些丫鬟都是本本分分的人。丫鬟与丫鬟之间可能会出现相互争斗的事,丫鬟也可能如《红楼梦》中的红玉与司棋一样对男子有思慕之情,但绝不会出现丫鬟在其中穿针引线,大胆地将自己的小姐与陌生的男子生硬地撮合在一起的情况。可见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丫鬟设置也明显不合情理。才子佳人小说不过是将女主委托于高门,其完全不符合世家大族的真实情况。所以贾母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才子佳人小说里的故事诌掉了下巴,都是编书人前言不搭后语的胡编乱造。也就是顽石所批判的“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贾母认为才子佳人小说都是那些妒人富贵的人,或因为追求富贵人家的女儿被其拒绝的人,编出这些风月淫滥的故事来污蔑富人家的小姐。还有些人因为看才子佳人小说类的书着了魔,自己也想要有这样的佳人如同小说里写的一样供其取乐赏玩,便也胡编乱写起来。这些写书人并不知世宦诗礼大家真正的礼仪教养,贾母最后讲明了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这些事不仅在世宦的诗礼大家没有发生过,就是在中等人家也不可能发生。这不过是市井上胡诌出来的混账玩意。可悲的是这些才子佳人小说让天下人真觉得富贵人家的子女如才子佳人小说所写的那样轻薄放荡。才子佳人小说又是这些读圣贤书的男子所编的故事,可见这些读书人一天念了些什么书,这就如第八回贾政骂贾宝玉的话。“……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话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红楼梦第八回》)提到精致的淘气,让笔者突然想到现今流行的一个词——粗致的利己主义。精致的淘气就是只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我行我素,这不就是粗致的利己主义吗?读到这里,相信各位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贾宝玉要骂那些读书人是国贼禄蠹了吧?我们很多人将贾宝玉骂国贼禄蠹解说成是骂儒家骂孔子,真是一派胡言。纵观《红楼梦》全文,我们找不到贾宝玉骂孔孟及《四书》的一句话,他每每面对这些圣人及圣人之言时,都是毕恭毕敬。贾宝玉所骂的是那些曲解圣人言,还编写些混话乱语来祸害世人的读腐了书的人。这些读腐了书的人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祸害,他们为了一己之私而写出危害天下的文章来。贾宝玉所骂的就是那些只为了自己的利己主义者。注意笔者这里用了“只”字,人生当然要为自己,但是不能只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更当有为天下苍生计的抱负,而不能只为一己私欲胡作非为,胡写乱注,祸害后世。很多人将崔莺莺的行为解读为追求爱情的典范,把这种行为当成是典范的男子哪里是为了女儿,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想让更多的女儿像崔莺莺一样来追自己,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淫,这样的人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宣扬崔莺莺行为的女性,其实是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而今多少自恋的人皆会替异性心中取中自己,这其实就是大肆宣扬才子佳人小说造成的。当警幻仙子提到“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时。戚序本与蒙府本夹批写道:色而不淫四字一连属于各小说中,今却特贩其说批驳出矫饰之非,可谓至切至当,以环形重任,勿谓前人之矫词所感也。多少人受这些矫饰之词的影响,信了才子佳人小说所写的鬼话,很多人都被其中的爱情感动得稀里哗啦,却深中其毒而不自知。世人是如何深受才子佳人小说影响的呢?作者着重通过林黛玉的一生写了出来,我们会在后面的文章中详细分析。才子佳人小说对世人的毒害,在当今社会依然深重。多少人不是受着前人矫非饰丑之词所感发,最终陷入情的虚幻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批书人所用的“感”字,这里的感是我们通过眼看耳听等感官所感而获得的知与识,将这种知识当成了真,最终没有回归到无知无识的本心本性之中,没有使自己的心不动,而是使自己心动,就会受着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深陷情之泥淖而不能自拔。最后也就不能辨真去伪,信了书中的鬼话。此感获得的知与识是没有接近天理与天道的知与识。因为没有识别前人掩丑饰非之矫词,只被那轰轰烈烈的表象所感,被隐藏在背后的淫所迷,被一两首情诗艳赋所惑,以至于发而不能中节,过分地夸大了情的功效,最终受着淫的主导,陷入别人设计的陷阱之中,让自己变成了轻薄之人。才子佳人小说的另一个巨大危害,是使世人将才子佳人小说所写的世家大族,当成中国古代的真正诗社簪缨之族。现今解《红楼梦》者,大都以才子佳人小说所写对标《红楼梦》中的诗礼簪缨之族的文化底蕴,最终得出的结论便是对中华真正文化的曲解,这便是解读中华文化的最大悲哀。以才子佳人小说解诗礼簪缨之族的文化又如何能复兴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被这群不肖子孙解读得不成人样,天天喊骂着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这些人压根就没有搞清中国古代的世家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就只用一句骂涵盖所有,真是有辱华夏千年文明,可悲可叹可恨!中国古代的世家大族完全不是我们现在世人用才子佳人小说所理解出来的样貌,其有极深的文化底蕴。要振兴中华文明,我们必须要挖掘出这底蕴来。历来野史、风月笔墨以及才子佳人小说,将天下诗礼人家的女儿贬得极其不堪。这些文字更贻害了后世富贵人家的子女,他们读这些书后争相效仿,使后世男儿变成了风流纨绔,后世女儿变为流荡女子,这些人玷污了富贵之家该有的诗书礼仪。曹雪芹看到世上文人如此涂毒笔墨,所以他要开生面立新场:“……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红楼梦第一回》)才子佳人小说全是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是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这些人被包装成知书识礼的才人,干的却是淫逸的事。这些小说在不断美化淫的行为中,引得天下不明缘由的儿女争相效仿,只顾谋虚逐妄,真是误尽天下儿女。所以作者想用《红楼梦》一文打破熟套之旧稿,让世人破愁醒盹,不再去谋虚逐妄。曹雪芹要为闺阁昭传,写出与历来野史、风月笔墨以及才子佳人小说不同的文章来,让世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世家文化,让世人知晓真正的富贵之家的女儿到底是什么样的,让世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情。在甄士隐的梦中,茫茫大士与渺渺真人的对话中也阐明了作者破陈腐旧套的观点:那道人道:“果是罕闻,实未闻有还泪之说。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那僧道:“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红楼梦第一回》)《红楼梦》所述之情与历来风流人物的偷香窃玉,暗约私奔的风月故事完全不同,历来的风月故事如警幻仙子所说都是在饰非掩丑。这些故事将男女之事只是简单地归为情之所至,最终都免不了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的淫,这些人不过是为了沉溺在情欲之中而矫饰其淫。他们所述的并非人间真情。至于闺阁中的一饮一食,他们更不会记叙。曹雪芹要证人间真情,让世人以情悟道、守理衷情。所以《红楼梦》一干人入世后,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处,全与前人传述的不同。希望世人不要再为好色不淫张目。《西厢记》里的张生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如果认为可夸,就问一句,当你看完了《西厢记》全文后,了解了张生的人品,假设崔莺莺是你的女儿,你处在崔莺莺父母的处境下,你愿不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如果你愿意,那你就夸吧。如果你不愿意,那就请你不要再宣扬为了追求所谓的自由爱情而祸害别人家的儿女。宣扬崔莺莺的行为实在是太可恶了,当今无数少男少女被一见钟情给毒害。特别是女儿被毒害更深,损失更大。无数女儿受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用情极深,到头来发现不过是为了附和男儿之淫。仅凭只见一面就共赴终身,真是荒谬至极。世人切记曹雪芹所嘱: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我们可以用鲁迅在《二十四孝图》里所说的一句话,对世上的某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作结:“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注释: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9页。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73页。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73页。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73页。王实甫著、张燕瑾校注《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73页。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一一五页。注:本文由张延安(幽之鸣)原创,欢迎转载并保留版权。
标签: